沂蒙精神与沂蒙文学的互源、互塑关系可概括为“三个互为”:互为表里、互为生发、互为塑造。习有关沂蒙精神特质(“水融,生死与共”)的科学界定,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针对沂蒙精神所做出的详细阐释,在主题实践向度和方法论上,为当代沂蒙文学特别是其中的革命历史题材写作指明了发展趋势。但沂蒙文学对沂蒙精神的表达,并非空喊口号或直接作意识形态图解,而是以语言(美学形式)与形象(审美想象)打动人,感染人。沂蒙精神与沂蒙文学互源、互塑的历史突出地体现为对“当代性”的实践。然而,由于作家们对其理解不同,从而在历史演进中呈现了不同风貌。在“十七年”时期,其互源、互塑模式整齐划一,影响甚大,但也不乏弊端;在新时期,奉献与觉醒作为沂蒙文学的两大主题,使得沂蒙文学、沂蒙精神深入人心,但又因艺术创新力困乏而难有持续的发展力;九十年代以来,其互源与互塑止步不前,理性有余而灵性不足,创新亦相当乏力;新世纪以来,沂蒙文学以“临沂诗人群”为先锋,以赵德发、夏立君、江非、高军等几位实力作家为骨干,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纬度上,为二者互源、互塑关系开启了新路径、新可能。
何谓沂蒙精神?有关这方面的界定、生成演变、价值与意义的阐释,当以习的阐述最具权威性、纲领性、指导性:“山东是革命老区,有着光荣传统,水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对我们今天抓党的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1]在此,他不但将沂蒙精神的特质高度概括为“水融,生死与共”,还将之上升为党和国家精神文明建设高度并予以诊视,并特别强调“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对近,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撰文指出,“水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深刻揭示了沂蒙精神的科学内涵”,“充分揭示了沂蒙精神形成的深层原因”,“生动诠释了党和人民生死相依的血肉联系”,“深入回答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永恒课题”[2]。从习的讲话到刘家义的撰文阐释,这就分别从国家到地方(省)层面完成了对“沂蒙精神”特质、价值及意义的科学界定与最新阐释。更为关键的是,关于如何践行沂蒙精神,无论习强调“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还是刘家义号召“用心讲好沂蒙精神的感人故事”以及“倾力打造沂蒙精神的文化品牌”,在笔者看来,都无不强调要以主体观念、发展眼光、创造性思维凸显其当代品质。毫无疑问,这种界定或阐释在方法论和主题实践向度上为山东文艺特别是沂蒙文艺指明了发展趋势,而作为沂蒙文艺重要组成部分的沂蒙文学当然更当率先垂范。
何谓沂蒙和沂蒙文学?一直以来,专家学者们对其外延与内涵的界定或阐释并不一致。一种是侧重从地理或人文地理学上的界定,比如:“在地图上,山东至今没有沂蒙山这样一座山,说‘一群山’也似乎不完全确切,开始有‘南沂蒙’、‘北沂蒙’之分,指从沂水到蒙阴一带的一片山区;进而可以说指整个鲁中地区。再后鲁中、滨海、鲁南合并为鲁中南地区,‘鲁中南地区’,看来能够说是‘沂蒙’的广义概念。建国后,鲁中南地区撤销,不管专区、地区和城市怎样变化,也不管有的县市单立(如莱芜、日照),或有的县市划归了邻近地市(如沂源),仍大体以老鲁中南地区为范围(中心又是临沂市地区),还是较为合情合理的。”[3]一种是打破地理边界而侧重从文化角度所做出的界定,比如:“沂蒙文化的区域,以今天的行政区划来看,包括今临沂市、日照市全境及沂源、临朐、新泰、诸城、驿城、赣榆、东海、新沂、邳县等县区,即鲁东南地区和江苏部分地区,史称‘齐鲁锁钥’,是南北地域文化互渐、交融的结合部。”[4]但不管哪种界定,从地理或行政区划上来看,如今的临沂、日照全境或曰以汶河、沂河、沭河、蒙山等核心地理范畴的延展区域,应是沂蒙文化生成与演进最为核心、最为本源的物理空间。依托这样的地理空间或文化空间,经由漫长时间沉淀或凝聚所生成的带有区域共同体趋向的文学即沂蒙文学。地域性、民族性、现代性、革命文化/文学的主导性,作为界定或阐释沂蒙文学外延和内涵的四个常见向度而在实践中予以凸显。比如,已故老诗人苗得雨认为“沂蒙文学,是民族传统与革命传统融汇在一起发展成的带有地域色彩的一种文化艺术形态”[5]。他对“沂蒙文学”的界定至少包括地域性、民族性、革命文化的主导性这三重内涵。
沂蒙文学与沂蒙精神有何关联?可概括三个“互为”:互为表里,互为生发,互为塑造。或者说,二者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离。对作家而言:沂蒙精神是沂蒙文学表达的总主题,从方法论和主题表达向度上来说,不会存在多少争议;实然存在的沂蒙精神与被概念化的沂蒙精神显然是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背景、依据或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提纯、概括或衍生。因此,“沂蒙精神”就是不断被提纯和概括的时间沉淀物或历史衍生品。这就决定了作家们对沂蒙精神的理解与文本实践并非囿于一点或一隅,而总是以联系的发展的辩证思维不断对之进行审视或建构,从而继承并丰富其本体内涵。事实上,沂蒙精神既有其稳定的一面,也有其一直在变化发展的一面,而就后者而言,它又总是与历史演进的潮汐互为关联,诚如王万森所言:“耕读文化中,它是勤俭纯朴和崇尚文明的;抗灾和抗匪文化中,它是坚韧勇敢的;战争文化中,它是向往正义和敢于奉献的;特别看到,在多灾多难的历史变迁和新旧交替的文化转型中,它既是开拓进取的,又是和谐宽容的。”[6]然而,由于它与二十世纪革命历史进程的“水融,生死与共”,从而使得红色革命文化一枝独秀,并成为主导其他文化形态萌芽与演变的核心力量。由此以来,以革命和建设为中心所形成的红色文化以及由此而孕育或衍生出来的沂蒙精神[7],不仅是当代沂蒙文化也是当代中国最具特色、最具影响力的地域文化形态。在此统摄下,作为沂蒙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沂蒙文学,不仅其精神之根当然会扎根于此并从中获取丰厚的养料,从而生成众多以带有红色风格的优秀作家、作品,而且其对沂蒙精神的传承或重塑——奉献与忠诚,军民生死与共——自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在“十七年”期间,以王安友的《李二嫂改嫁》、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吴强的《红日》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品,以对沂蒙红色革命历史或沂蒙人民生活与精神风貌变迁史的书写而成为国家宏大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很好的例证。其中,现实中的众多“沂蒙红嫂”一经作家们的艺术塑造——刘知侠的《红嫂》[8]影响最大——自从成为文学角色那一刻起,便已深入人心,并成为沂蒙文学的独有标志;其纯朴、高尚的女性品质和自觉的奉献精神,亦大大丰富了沂蒙精神的本体内涵。如今,作为文化符号的“红嫂”,不仅成为沂蒙文化、沂蒙精神的一张名片,昭示着革命战争年代千千万万沂蒙儿女为中国革命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也作为党和国家层面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显示了沂蒙与新生共和国之间的血脉相连、生死与共的精神共同体关系。1949年10月1日后,一个展新的、震撼人心的“当代”生成了。在整个“十七年”时期,作为一个地域的沂蒙文学、沂蒙精神,不仅从来也没有缺席共和国宏大叙事进程,还以其后发优势成为中国最具活力、成就最突出、平台最高的地域文学之一而备受瞩目。沂蒙文学也就在这一段时间范畴内,与压抑中的现代性快速告别[9],从而快速开启了真正属于自身个人的文学史时代。
新时期以后,真正推进沂蒙文学发生质变,并有效进入文学现场中心地带的,则是以李存葆、刘玉堂、赵德发、王鼎钧、王兆军等作家带有一定反思性或启蒙性的写作。假如没有他们,作为史之意义的当代沂蒙文学就很难成立。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刘玉堂的“钓鱼台人物系列”和《乡村温柔》、赵德发的《通腿儿》和“农民三部曲”、王兆军的《拂晓前的葬礼》、苗长水的《非凡的大姨》都是该时期的代表作。从整体上来看,沂蒙文学与沂蒙精神密切关联的主题向度突出表现在:对故土之爱(风物、风俗、风景,等等)和人性之美的书写;对沂蒙老百姓和子弟兵无私奉献精神的展现;对人与时代关系的书写中,侧重揭示在社会转向大潮下人们的觉醒意识。历史理性与人文关照作为审视历史与现实的现代性思维、方法,已逐渐被广大沂蒙作家所采纳。他们的写作当然是典型的“当代性”实践。沂蒙文学中人学思想、批判意识的萌生并逐渐展开,正是得益于这作家的探索与实践。人性纬度或人道主义思想在文学中的展开,也即映照了现实中作为主体的人的解放。文学率先介入大时代潮流中,为沂蒙精神注入新质。这都充分说明,沂蒙文学又不仅深受红色文化的影响,它还向其周边和深处继续拓展、深扎。同时,这也都表明,有关何谓“当代”或“当代性”的实践,即从对“十七年”文学一体化规范的坚决贯彻(比如吴强的《红日》、刘知侠的《红嫂》),到八十年代以来对此种规范的大胆突破(比如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王兆军的《拂晓前的葬礼》),沂蒙作家都走在了当代文学发展的最前沿。
九十年代以后,特别是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间,沂蒙文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对“当代性”的实践最突出表现在宏大叙事逐渐退场,而代之以在诗歌、散文(含报告文学)、小小说等领域内个人化写作风潮的兴起。“当代性”与九十年代沂蒙文学、新世纪沂蒙文学的深度关联突出表现在,彰显个体之“我”在“时间”里的独立性、主体性,以及由此而展开的对于沂蒙历史与现实的再反思、再书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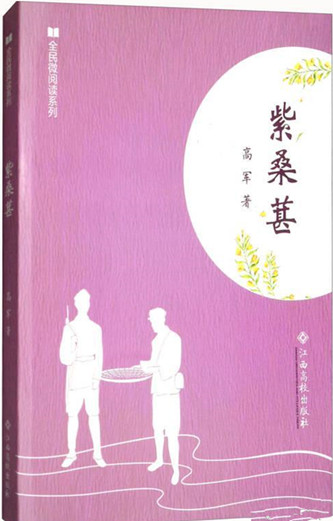

首先,以个人视角再述“红色沂蒙”,重塑沂蒙精神的当代品质。沂蒙革命历史堪称沂蒙文学的素材库。代表作有高军的小小说、苗长水的沂蒙山系列、铁流的《见证:中国乡村红色群落传奇》《一个村庄的抗战》、管虎的《斗牛》(电影剧本)等等。这种写作集历史考证、初心(信仰)追溯、可观的阅读(传播力)于一体,也形成了沂蒙文学特有的当代品质。其中,高军作为小小说领域内的领军人物[10],创作了大量以沂蒙革命历史、各类人物为题材的作品。个性化的人物,生动的细节,好看的故事,有教育意义的主题,等等,构成了高军小小说的几个突出特征。他的小小说继承了“红色沂蒙”叙事传统,又不乏鲜活的“当代性”,比较充分地表现了以“红色精神”为主导的沂蒙文化的地域魅力。管虎的《斗牛》从民间视角讲述妞儿、九儿等沂蒙山小人物的抗战故事,其对沂蒙精神的原生态呈现,极具感染力。影片中的牛二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乡间小人物,但他照料那匹奶牛胜过关心自己,他用挤下的牛奶救活了很多的饥民,他机智地与土匪、鬼子周旋,他不抛弃信义矢志不移地完成部队嘱托下的任务。这部影片将沂蒙老百姓的朴实本色和人间大爱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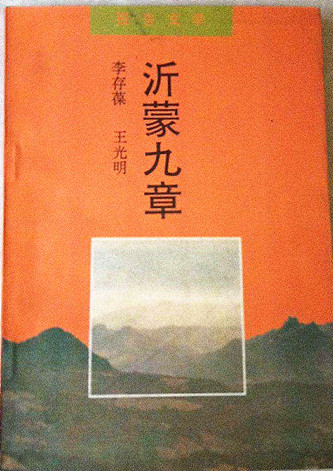
其次,视点下沉,将“我”自立为主体,并以此开启书写“新沂蒙人”的文学时代。如果说李存葆的《沂蒙九章》、高振的《沂水拖蓝》等散文(含报告文学)率先垂范,展开对“新沂蒙”的书写,尚处于由宏大叙事向个体书写转型中的话,那么,真正引发沂蒙文学发生巨变,彻底落实于个体表达,并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的当属诗歌创作,即以江非、邰筐、轩辕轼轲、尤克利、辰水、老四、风言、瓦刀、也果、子敬、曹玉霞、梅林等为代表的“临沂诗人群”,从对“口语诗”的探索与实践开始,逐渐形成包容各种形态、风格的新诗创作格局,从而为沂蒙文学、沂蒙精神再次有效挨近或跨入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心地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作为“临沂诗人群”领军者的江非对更新沂蒙诗歌的形象,对拓展沂蒙精神在“新时代”的内涵,更具有根本性的推动力。这是因为,与邰筐与轩辕轼轲的纯粹“小我”视角、意识及无根性写作不同,江非在“小我”和“大我”之间[11],不仅较为完整地继承自新时期以来的诗歌传统,还在对新乡土(“平墩湖”)、“物自体”、内面风景等诸多视域的创造性书写而自创一体,从而在诗歌史和文体特质上展现出更具可阐释、可建设的价值。老四[12],作为“临沂诗人群”80后代表,他以诗歌方式展开对人之本性(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个体心灵史(漂泊、孤独、疼痛)和生活本质(荒谬、悖论)的探察,以及对以汶河、蒙山为中心的地域文化史,特别是深置于其中的人、事、物及其本源关系的深度开掘与书写,都因别开生面、自成一景而备受业界瞩目。从艺术实践来看,其在地性、代偿性、及物性、偏于形而上的写作方式和美学姿态,不受任何形式和修辞的羁绊且以精当把握和精准表达为特质的文本实践,以及在都市与乡土或中心与边缘之间试图建构新式空间诗学的艺术抱负,更使其在同代诗人群体中显得卓尔不群。老四及其诗歌不仅有效、有力拓展了当代沂蒙文学的边界并为其发展注入新质、新貌,也因生成了一种被称为“老四诗学”的新范式——以诗学化的身体和身体语言探究生活与存在本质;以粗粝而沉重、尖锐而忧伤、通透而忧郁的话语风格而自成一体;尤长于对现实与梦想、温暖与疼痛、和谐与悖谬等既日常又复杂、既统一又矛盾的“经验域”或“内视界”的深入开掘——而让人对之寄予更多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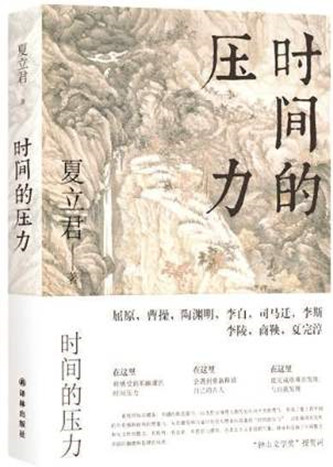
再次,沂蒙文学的开放性、大气象也初步彰显。据笔者阅读视野,在新世纪以来的沂蒙文坛上,能在写作中展现大气象、大格局的当属散文家夏立君[13]。夏立君及其散文写作,典型地体现了沂蒙文学或沂蒙精神“既有黄河文化的沉实,又有滨海文化的开放”[14]的特征。他对对中国古典文人的解读,他的新乡土写作以及游记写作,都无不贯彻着对“时间”与生命的本体性探讨。这种审美姿态与艺术穿透力,在现当代沂蒙文学史上,也绝无仅有。人类从未放弃过对于时间的体悟与描述,但若要给“时间”下一个准确定义或者说对其外延与内涵做个准确界定,大概是一个具有相当难度且永远也没法完结的课题。与物理领域内的把握与界定不同,文学(作家)与时间的关系却是具体的、形象的、可把握的:从孔子的“逝者如斯夫”到庄子“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隙”,从鲁迅的“时间就象海绵里的水”到朱自清的“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再到夏立君的“时间的压力”、“时间之箭”、“时间会说话”,都可看出,他们的“时间”已非历时的、一维的、不可逆的,而是共时的、多维的、可折叠的。作家们改变了“时间”的物理属性,故可以自由出入任何“时间单元”。夏立君也是这样一位自由出入于“时间单元”并以“时间”为伴侣、为攀谈者、为灵感来源、为灵魂归宿的文化探寻者、精神建构者、散文书写者。或者说,对夏立君而言,时间作为一个历史、美学与精神的符码,构成了他及其文学实践的源头性的、统摄性的存在。他的《时间的压力》、《时间会说话》亦然。“时间”以及“时间话语”是其最为核心的主题向度。他在修辞策略上对“时间主题”做了艺术转化,即将时间的“直接呈示”转化为时间的“空间表达”;而无论怎样表达,表达什么,却又都不脱离当代性视野。即,他将“刘家庄时间”、“长河时间”、“喀什时间”重叠或并置于当下,并在当代意识的烛照下,展开对乡愁、生命、历史、古人的再度书写。这种书写不仅直接表达一己所想、所念、所思、所忆,也对当代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新世纪以来,沂蒙文学的“当代性”实践进入“快车道”,若单从沂蒙精神与沂蒙文学互源关系方面考量,我觉得如下四类写作具有不可或缺的典范意义:一类是沂蒙当地作家的基于历史经历和生命实感的代偿性写作。比如,沂南的王秀云、尤克利、梅林、武庆丽[15],蒙阴的乔洪涛、彭兴凯,兰陵的辰水。他们从事写作的原因,无非正如方方所言:“我喜欢它的理由只源于我自己的熟悉。因为,把全世界的城市都放到我的面前,我却只熟悉它。就仿佛许多的人向你走来,在无数陌生的面孔中,只有一张脸笑盈盈地对着你,向你露出你熟悉的笑意。这张脸就是武汉。”[16]若将引文中的“武汉”改成沂南、蒙阴或兰陵,并将之用来表述他们与这座城的关系,也大可适用。是的,他们之于故乡,因熟悉而爱,并因之而写。这类作家因对“三画”[17]的描写和“四彩”中对于“自然色彩”、“悲彩”美学基调的实践,以及更切近乡土肌理的内涉型表达,而赋予沂蒙文学以更为纯粹的质地,对沂蒙民间精神的传递、塑造,远比其它作家展现得更为直接、充分、厚实。一类是沂蒙领军人物着眼于历史或时代的带有穿越时空区隔的展现大气象的写作。比如夏立君的《时间会说话》、赵德发的《经山海》。两位作家的写作分别展现了沂蒙精神中“沉实”和“开放”之特质,其对宣扬或重铸沂蒙精神的当代性品质,都发挥了其无法替代的作用[18]。同时,这类作家的创作已大大超出沂蒙文学内涵与外延的框定,而进驻中国当代文学现场的中心地带,从赋予沂蒙文学以崭新形象,为新时代沂蒙精神的传播注入活力。还有一类是非沂蒙籍的作家或远离故乡的沂蒙籍作家针对沂蒙题材(特别是革命历史)所展开的再审式创作。比如杨文学的《沂蒙山小调》(上、下)、房伟的沂蒙抗战系列短篇小说[19]、赵冬苓的《沂蒙》(电视剧剧本)、常芳的长篇小说《第五战区》、王兆军的《黑墩屯——一个中国村庄的历史素描》、周朝军的《九月火车》。这类作家再度聚焦、审视沂蒙革命历史,以“真实,好看,有意味” [20]为审美追求,从而开拓了革命历史题材写作的新路径、新可能。同时,他们视野开阔,常常打通现实与历史、官方与民间之间的森严壁垒,转而在艺术层面上将对沂蒙精神开掘或表现引向新征程。上述四类作家的写作因受到读者广泛关注从而为沂蒙精神的广为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沂蒙文学的“当代性”实践,不仅是对沂蒙文化、沂蒙精神展开溯源性书写的历史,同时也是不断对其进行“保值”或“增值”的活动。如果从某一时段或局部来审视沂蒙文学“当代性”实践的即时效果,以及沂蒙文学和沂蒙精神的互源关系,都可以说发挥到了极致,然而,“极致”并不代表永远有效。沂蒙作家总会深陷某种习焉不察的误区,即对“当代性”的理解总会定于一端而不顾其余。诚如陈晓明所言:“‘当代性’说到底是主体意识到的历史深度,是主体向着历史生成建构起来的一种叙事关系,在建构起‘当代’的意义时,现时超越了年代学的规划,给予‘当代’特殊的含义。”[21]如以此标准来检验他们的创作,很难说他们都达到了“主体意识到的历史深度”,且“超越了年代学的规划,给予‘当代’特殊的含义”。实际上,任何形态的地域文学不能离开赖以栖身其中的地域文化。沂蒙文学作为一种深受多种文化影响的文学形态,其内在构成、演变、影响也并非铁板一块。单就沂蒙红色文化而言,其对沂蒙文学的支撑、塑造是显而易见的;同样,沂蒙文学深扎于沂蒙红色文化的土壤中,并源源不断地生成新文本,其对包括红色文化在内的沂蒙文化/沂蒙精神的创造性继承或反哺式塑造亦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沂蒙文学的生成与发展并非是自足性的,而沦为沂蒙红色文化或“十七年”红色经典谱系中的附属,即只有依赖“他者”力量,并被编入“他者”谱系时,它才获得“新生”。比如,刘知侠的《红嫂》、吴强的《红日》、苗得雨的一些诗歌,等等,一旦离开主流意识形态阐释,其实都很难获得文学史的再度认同或者从中被阐释出超越于时代与文本的新意来。这说明,在新时期以前,沂蒙文学与沂蒙红色精神基本处于同步发展状态,其互源、互塑关系是高度统一的。由这种“统一”所造成的优长与弊端,都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即当爱党爱军、军民鱼水情、舍小我,顾大我(集体主义、)等带有突出国家集体话语或革命话语风格的文学实践,在以刘知侠的《红嫂》、吴强的《红日》、李存宝的《高山下的花环》为代表的经典文本中,借助历史激情和鲜活典型而得到一边倒的集中表达后,其后续发展力终因主体对历史体验的不足或艺术理念的落后而难有可持续发展力。其实,对某种外在理念的贯彻或图解本不应该是文学第一性要求——对文学而言,追求“艺术真实”、情节或细节建构上的合理合情、语言或文体上的探索,等等,永远是第一位的——但沂蒙作家却在这方面耗尽了心血。这种艺术实践上的南辕北辙,以及密切关联或直接图解主流意识形态的鲜明的实践向度,都使得沂蒙文学因缺乏艺术上的创新性而难以在文学史上拥有跨越时代的增值性阐释价值。自1990年代以来的三十多年间,沂蒙文学趋向多元发展,迎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高扬精英意识的个体化写作、皈依商业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写作各有“市场”,但各自对“当代性”的理解与实践又大都误入歧途:迎合主流一脉重视图解理念(比如“新时代”)赢得了“当局”,却失去了“读者”;精英写作太确信“个人化”以及由此而生成的主体思想介入时代和精神领域的力量,结果也同样因为读与写的不通约性而处于孤立状态;至于大众化写作一脉则彻底拥抱市场,把文学等同于“为人民币”而写作的交换活动,则已越出文学范畴而不在本论文讨论的论题内。总之,该时期沂蒙文学对“当代性”的理解与实践,同样存在极端化倾向。那么,该如何纠正上述误区呢?在今天,沂蒙文学对沂蒙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当有更大作为,其关键就在于对“当代性”的切实理解与创造性实践。
其一,在认识论上,亟待深度拓展。沂蒙文学对沂蒙精神的表达,沂蒙精神对沂蒙文学的支撑,彼此之间的互源、互映、互塑从来不是单向或单线展开的,而总是以多向、立体、交互的感应模式而存在着,而发展着,故对沂蒙文学或沂蒙精神“当代性”的理解和实践,既不能囿于对“十七年”和新时期两类话语装置的概念化框定,也要警惕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因消费文化复兴而逐渐生成的历史虚无主义与价值虚无主义两类后现代思潮的负面侵袭,从而突破种种拘囿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有实质性进展。事实上,因为沂蒙精神“既有黄河文化的沉实,又有滨海文化的开放”[22],那么,沂蒙文学对沂蒙精神的表达也理应更为自由和广阔。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两者彼此间的交互关联却步履蹒跚,时常形同陌路。沂蒙作家对主流价值观的颠覆与戏仿,曾一度成为“时尚”。这也在表明,从紧随主流意识形态一路走来的沂蒙文学、沂蒙精神,在面向今天和未来时遭遇到了发展的瓶颈问题。新世纪以来,“开放”作为沂蒙文学和沂蒙精神最具时代特质的品质,只在诗歌和散文界少数几位作家笔下得到一定效果呼应、实践。对绝大部分作家而言,对“当代性”的理解与实践并无多大起色——反复重复过往主题,建构力很有限,艺术手法很陈旧。在这种境况下,沂蒙文学与沂蒙精神的互源、互塑自然就是效力甚微。陈晓明说:“在文学上(和美学上),要认定‘当代’却并不是特别容易。80年代后期,为了对时代的审美变化加以把握,人们划分出‘后现代’这种观点,相对于整个‘现代’,‘后现代’显然更具有‘当代性’,‘后现代’就是‘当代’,但是‘当代’不一定就是‘后现代’。这就是中国语境,‘当代’一词表示的时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包含了‘当代’中国特有的历史感及其时间意识。[23]”中国语境中的“当代性”既表现为自“十七年”时期一体化实践,也表现为自“新时期”以来一体化解体过程,而“当下”、“当前”、“未来”等也理应内在于其肌理之内。据此,作者觉得,沂蒙文学中的“当代性”更应当是一个绵延性的指向宽广的时间意识,是将历史、现实、未来统一于“当下”并以此反应、揭示或呈现时空存在之样、之态、之谜的艺术实践。我们强调文学创作要有历史感、现实感,说白了,也就要求作家具备打通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创造能力,从而完成对于历史或现实的总体性观照或预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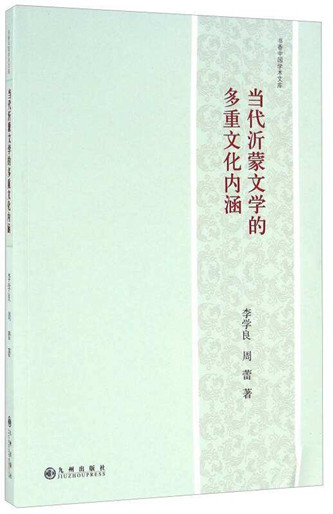
其二,在方法论(美学观念)上,亟待理念更新。沂蒙作家的文学创作又都有其明显缺失——理性有余(主题的先入为主)而文学性稀薄。而更多时候,沂蒙作家所谓“当代性”的实践又陷入另一种偏狭,即只注重“写什么”上的大胆开掘,而忽略了在“怎么写”上的艺术探索。也就是说,不是不能写(写什么),而是“怎么写”依然是困扰沂蒙作家的最要紧的麻烦——比如,同样是红色革命题材,王愿坚创作于“十七年”时期的那些短篇小说,在今天读来,依然常读常新,为什么呢?作为主旋律写作的代表,柳青、孙犁、赵树理、路遥等作家的作品在今天依然备受各阶层读者喜爱,其原因尤值得细细考察。而沂蒙作家在从事类似题材或主题的写作时,却总难以处理好这一问题。这其中有几个误区确有再次重提的必要。首先,对“真实”或“真实性”的机械式理解,即把文学真实等同于生活真实,而不是“艺术真实”。当前,强调扎根生活,加强现实题材创作,其前提是如何理解“生活”、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互文关系。若四者不相容,一切写作都无效或效果大打折扣。其实,扎根基层,熟悉生活,是从事现实题材写作的基本前提;生活累积到某些特定的程度,需经过提纯或审美转化,是从事这方面写作的关键;运用精当的艺术形式,将之物化为独一无二的语言文本,是昭示写作成功的唯一标志;以文本为媒介彼此间生成对话与共鸣,是该文本能进入文学经典化通道的必要条件。沂蒙作家对于上述四个环节的理解与实践普遍不到位。其次,在革命历史题材写作中,把无限靠近那个“历史真实”作为第一性追求而弱化或不考量文本自足性问题。其实,这一问题已被文艺理论家讲得很清楚了——“现在有一种误区,写的作家认为自身是在普及历史知识,看的读者认为能增长历史知识,这完全是误会。历史题材的创作属于文学文化,它不提供真实的历史知识,它提供所选定的历史框架、历史时限的真实的艺术形象,它的功能主要是审美欣赏,不是普及历史知识。如果真想了解历史知识,还是要去看历史教科书。”[24]——此不再赘言。再次,在对历史题材书写中,不善处理或难以驾驭历史理性和人文追求之间的艺术张力。最后,文体意识薄弱,探索与实践能力相当不足[25],对“形式即内容”(“有意味的形式”)的美学理念还相当隔膜。这些弊端都非一朝一日所能克服的。然而,真正的文学从来都是少数天才作家的事业,其在艺术实践上的独一无二性以及由此而昭示出的神启般的伟力,只有留待时间去见证了。
[1]《习在山东考察时强调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汇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正能量》,《人民日报》2013年11月29日第1版。
[2]刘家义:《弘扬沂蒙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学习时报》2019年10月30日第1版。
[3] [5]苗得雨:《“沂蒙精神”永在》,《文艺报》2006年3月14日第2版。
[4]韩延明:《沂蒙文化生成和演进的历史分期摭探》,《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6] [14] [22]王万森:《从文学视角观察沂蒙文化》,《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7]1990年,由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提出,即“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参阅周广聪、张帆:《沂蒙精神16字来源》,《齐鲁晚报》2011年7月27日第2版。
[9]现代沂蒙文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新文化运动,即由刘一梦、王思玷等早期沂蒙籍革命者的小说创作,可看作是现代沂蒙文学的发端。以写实性、批判性为特征的现代沂蒙文学在三四十年代被以革命斗争和战争文化所改造。待到新中国成立,作为一个地域的“沂蒙文学”在整体上被纳入“十七年”的语境中,从而出现由“现代性”向“当代性”的突转。
[10]高军,1962年生,临沂沂南人,现为沂南县作家协会主席。笔涉小小说、文学评论、文学史、诸葛亮研究等众多领域。代表作有《紫桑葚》(小小说集)、《沂南文学史》、《诸葛亮十八讲》。《紫桑葚》收入语文出版社出版的全国通用小学教材《语文》在全国十多个省区广泛使用。
[11]江非,1974年生,临沂河东区人,现居海南。著名诗人,参加过《诗刊》第十八届青春诗会,出版诗集《独角戏》、《纪念册》、《一只蚂蚁上路了》。
[12]原名吴永强,1985年4月出生,山东临沂人,居济南。中国作协会员,山东作协签约作家。著有诗集《孤独者说》《自白书》。曾获2014“紫金•人民文学之星”诗歌佳作奖,黄河口驻地诗人。
[13]夏立君,1962年生,临沂沂南人,著名散文家,现任日照市作家协会主席。著有散文集《时间的压力》、《时间会说话》。《时间的压力》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15]王秀云,小说家,著有《到山里拾柴禾》、《小城生活》;尤克利,诗人,著有诗集《晚秋》,曾获“全国农民十大诗人”称号;梅林,诗人,著有诗集《农事》;武庆丽,小说家,代表作有《失踪》、《大水》、《向日葵》。其中,《失踪》入选《中国当代经典必读2019年短篇小说卷》(吴义勤主编)。
[17]乡土小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文类。丁帆曾用“三画四彩”来概括其艺术特征:“三画”即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四彩”即自然色彩、神性色彩、流寓色彩、悲彩。见《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社,2007年版。
[18]夏立君的《时间的压力》、赵德发的《经山海》分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2019年“五个一工程”文学奖。作为土生土长的沂蒙作家,赵德发和夏立君的创作对践行并弘扬沂蒙精神,做出了重要贡献。
[19]房伟,山东滨州人,现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近年来,他创作了不少沂蒙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代表作有《小太君》、《副领事》、《肃魂》、《鬼子妮》等等,后收入小说集《猎舌师》,并以此获得“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2019年)。
[20][24]童庆炳:《历史题材创作的三向度》,《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
[21][23]陈晓明:《论文学的‘当代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6期。
[25]相比较而言,刘玉堂的幽默味(比如“钓鱼台人物系列”)、赵德发的方言实践(比如《通腿儿》)、夏立君的大文体探索(比如:《李白:忽然来了个李太白》、《屈原:第一个独唱的灵魂》),轩辕轼轲的口语诗,等等,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文章原发于《中国文化论衡》2020年第1辑,有微改。)
- 上一篇: 给牦牛挤奶_财经台
- 下一篇: 猪价欠好更要用加大饲料




